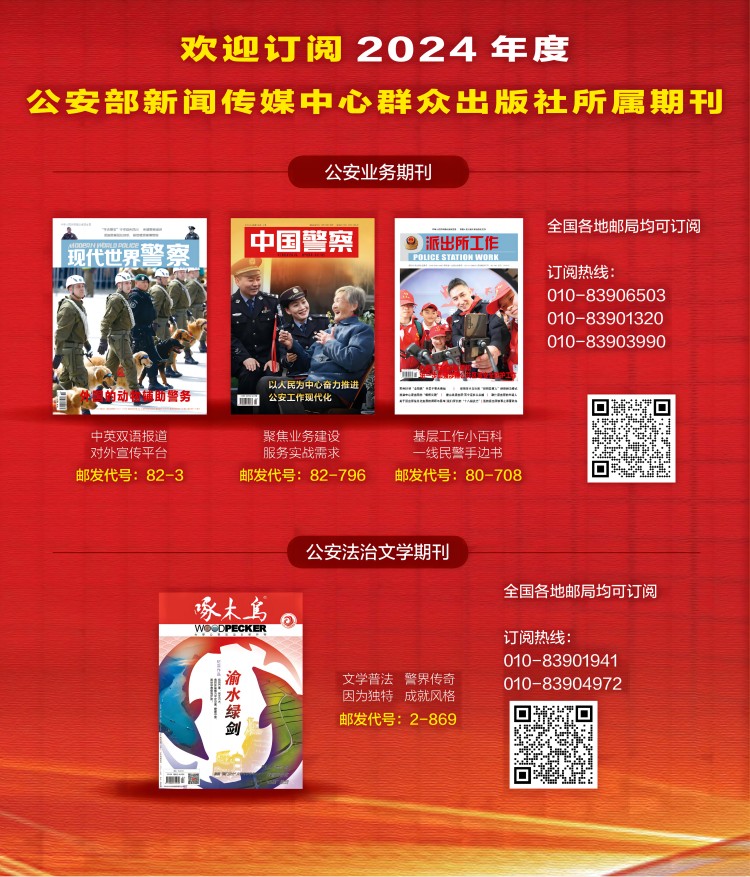在云南德宏边境禁毒一线,甘叔是大家敬仰的前辈。
5月29日,我们在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瑞丽大队见到了甘叔。
甘叔叫甘同堵,今年62岁。穿着一身橄榄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些。他耳朵有点背,跟他说话需要大点声。

队里的人都喜欢拉着甘叔讲讲过往的事。不仅因为在他那能听到像“毒贩运毒前要算‘鸡脚卦’”这样的趣事,更因为他经历了德宏禁毒几十年的历史。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东南亚“金三角”贩毒集团实施毒品北上、建立“中国通道”后,云南边境首当其冲,成为毒品渗透的必经之地。
1982年,云南成立专业禁毒队伍,掀开了禁毒的新篇章。处于边境一线的德宏,也在此时轰轰烈烈地展开禁毒斗争。
甘叔1981年入伍,没多久就赶上禁毒斗争的浪潮,开启了他的禁毒人生。他回忆,“这里的边境没有天然屏障,贩毒分子多是通过小路从缅甸那边背毒品进来。我们走山路去堵卡,多的时候一次能查到一二十公斤。”
一张老照片里,甘叔和4名战友并排站着,面前是一堵五颜六色的肥皂盒码成的墙,约两米多长、六七十厘米高。“这是2006年左右,我们从肥皂盒中查到了8公斤多海洛因,是3个人从小路背进来的,还带着枪。”

2015年,甘叔正式退休。队里的年轻民警说,甘叔是原公安边防部队服役满30年军龄、特批退休的正营职警官。
30余年,在毒情严峻、枪林弹雨中,甘叔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他已记不清这些年查获了多少毒品、抓获了多少毒品犯罪嫌疑人,唯有那些功勋章是无声的见证。
甘叔有讲不完的故事。但他最不愿讲的,是战友的牺牲。
“月亮石”之痛
牺牲,是禁毒绕不过去的字眼。
在德宏,谈起牺牲,则绕不开“月亮石”。
月亮石在盈江县支那乡,位于海拔2500米的山巅,是当地村民烧香拜佛、祈求幸福平安的一块石头。月亮石,多么美好的名字,却成了无数人不愿提起的痛。
5月28日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们跟随盈江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果京(化名)去往月亮石。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果京把车停在一个岔路口,走下车点了一支烟,沉默许久。
17年前,也是这条路,果京和战友们奔赴毒贩交货地点,执行抓捕任务。也是在这个岔路口,他眼睁睁看着战友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中一名战友徐胜前被子弹打穿腹部,我们把他从山上抬到这里,血流个不停,人到这里没了。”指着地上雨水流淌的方向,果京说,“当时他身上的手机响个不停,是他女朋友打来的,现场的人都哭了,大家都不敢接。”
思绪在大雨中蔓延。果京回忆,我们是3月25日凌晨3点出发的,开到现在的位置是5点。怕打草惊蛇,我们就下车徒步前行,走了7个多小时,才到达伏击地点。
雨越下越大,把山路冲刷出一条条沟壑。大雨声中,果京讲述着那场永生难忘的战斗,声音低沉,有时话像是被卡在喉咙里。
8人小分队到达伏击点不久,几名毒贩就出现在视线中,指挥员看准时机下达抓捕命令。然而,此时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毒贩开始疯狂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子弹从我头顶飞过,手榴弹就在我旁边不远爆炸。”果京回忆。

那场战役中,3人壮烈牺牲,3人身受重伤。牺牲的3人是白建刚、徐胜前、甘祖荣。
在之后的采访中,我们见到了“月亮石”战役中牺牲的甘祖荣的妹妹甘玉琴。从她口中,我们认识了甘祖荣,也听到了“接过你的枪继续战斗”的故事。
1982年,云南专业禁毒队伍成立的同年,甘祖荣出生在贵州毕节大山里的一个贫困家庭。甘玉琴回忆:“为养活一家,父亲去附近的煤矿打工,那时候煤矿上经常出事,我特别害怕,就跑到煤矿上,求他不要再去挖煤。”
甘祖荣考上大学却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放弃。后来,他应征入伍,成为德宏公安边防支队的一名战士,一是因为从小崇拜军人,二是部队有津贴可以补贴家用。“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洗衣机都是二哥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的。”甘玉琴说。而她自己,看不得父母受苦,坚持退学,外出打工。
从此,一家人聚少离多。甘祖荣到部队7年只回了3次家,但书信不断。甘玉琴永远忘不了2007年的春节,“那是最完美的一个春节,那年的团聚是二哥入伍后我们全家唯一一次大团圆,也是最后一次。”
春节休假结束后,甘祖荣回到部队。20天后,正在地里干农活的父母突然接到“甘祖荣在执行任务时受重伤”的消息,一家人立即启程赶往德宏。
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车停在殡仪馆门口时,心存的希望彻底被击碎,甘祖荣的母亲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直到那时,家里人才知道甘祖荣并非他说的“在部队搞后勤”,而是从事极度危险的缉毒工作。

部队领导来征求甘祖荣父母的意见:把烈士骨灰带回老家安葬,还是安葬在当地的烈士陵园?出乎甘玉琴的意料,母亲含着泪说:“祖荣热爱部队,他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就让他留在边疆吧。”
甘祖荣牺牲8个月后,甘玉琴通过了体检和考试,入伍来到了哥哥战斗过的云南德宏,成为一名公安边防战士。新兵训练结束后,甘玉琴被分配到木康边境检查站。
她痛恨毒品,也怕给哥哥丢脸,便拼命地工作,第二年便立下了三等功。难得休息可以下山,别的战友都去城里逛逛,甘玉琴则习惯买点吃的,到烈士陵园陪二哥聊聊天,“感觉他一直都在”。
如今,16年过去了,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已成长为派出所的缉毒业务骨干。在甘玉琴如今工作的户拉边境派出所,有一块“边关花木兰甘玉琴”的展板,上面写着:女性本柔,遇事则刚,她以英雄哥哥为榜样,接过哥哥手中的钢枪继续战斗……
“幺妹,你出门一年多,应该说学到了一些经验。回来的这段日子,为了这个家,真的辛苦你了,二哥很感激……”42岁的甘玉琴一字一句念着20年前甘祖荣的家书,失声痛哭。
甘玉琴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二哥入伍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与母亲的合影。照片中的甘祖荣左手搂着母亲的肩膀,一脸灿烂笑容,是个阳光大男孩。
是啊,他牺牲时也不过25岁。

“马赛克”人生
在媒体关于禁毒报道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脸上打着“马赛克”或是带着大大口罩的“蒙面人”,他们多是战斗在禁毒一线的警察。
田英(化名)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也是德宏禁毒战线响当当的人物,立过一等功,是云南省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初见田英,他不太愿意直面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警惕。这些年,因担心影响家人,他几乎没有和家人在公开场合一起出现过,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是小心翼翼,尽可能让自己“隐形”。
他皮肤黝黑,头发比普通民警要长一些,一身很随意的运动服。“干我们这行,不能看起来像军人或警察,要看起来像在外面混的人。”他指着脚上的运动鞋说,“要搞摸排侦查,这种干干净净的运动鞋就不行,当地人或缅甸人习惯穿夹脚趾的拖鞋,要了解他们的习俗。”
在禁毒情报、侦察战线上打拼了20余年,田英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比较难的是打入贩毒团伙卧底。有一次他充当马仔只身前往约定地点,被数名毒贩持刀围住,要检验他的身份。最终,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取得毒贩信任,并在同事协助下成功打掉一个贩毒团伙。
这类常人听来异常惊险的故事就是田英的工作日常。他还说,去谈“买卖”之前,一定要在装扮上下足功夫,比如手上要带上大戒指。“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过硬,对价格、行情、外面的局势等都要了解,不能说错一句话。”他说,每次任务必须要把每一个细节想到,不然稍一马虎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除了惊心动魄,更多的是等待的煎熬。有些毒品案子,要经营好几年。记忆中,他曾于夏日潮热和营营蚊虫中,在一个点上蹲守了3个月。
粗算一下,他干禁毒已超过了8000天,侦破毒品案件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00余名,查获各类毒品3000余公斤。
普通人难以真正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每一克毒品的背后都可能是流血牺牲,每一次抓捕毒贩都可能面临殊死搏斗。
缉毒警察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累累战功,只能深藏心里;无数勋章,只能悄悄放着;只要活着,就不能以真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面对的多是亡命之徒——毒贩恨他们,有毒枭给他们寄恐吓信,有的甚至扬言花重金买他们人头。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他想了想,答道:“没想太多,案子多破一个算一个。”见记者不解,他补充说:“你看,平常人去餐馆吃饭,首先想的是有什么好吃的。但我会不自觉地观察屋里的人,分析环境。不为什么,就是习惯如此。侦查、破案,成了一种习惯。”
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钻一行。
道理也许如此,但并未打消我们心中疑问: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他们为何选择无畏?
答案,也许像田英所说的“职业使然”……

生生不息
2022年,在云南专业禁毒队伍组建40周年之际,云南警方公布了60张牺牲的禁毒英雄照片。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尹胜男(化名)的哥哥尹铭志是其中之一。
1997年8月,尹铭志在抓捕毒贩时,为保护协助办案的群众,同多名手持凶器的毒贩英勇搏斗,身中10余刀依然紧紧抱住毒贩不放,最终壮烈牺牲。这一年,尹铭志只有22岁。
1998年12月,尹胜男入伍,成了缉毒战线上的一员。
哥哥牺牲10年后,月亮石战斗中,尹胜男又失去了另一个“哥哥”——她亲密的战友徐胜前。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尹胜男就有这样的价值追求。她很喜欢维和女警和志虹说的那句话——于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
20余年来,她参与侦破各类毒品案件100余起、查获毒品400余公斤,用赫赫战果告慰“哥哥们”。
有一次,她在追捕一名企图逃跑的女涉毒犯罪嫌疑人时,掉进2米多深的排粪沟,浑身沾满粪便,胳膊、脚都受伤了,后来到医院检查,发现当时她已怀有身孕。
“有时候执行完危险任务也会后怕,很多时候也会累到怀疑人生,但想想我哥,想想那些为禁毒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战友,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继续坚守下去。”尹胜男说。这大概是“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之问的又一个答案。
流血与牺牲,阻挡不了接续奋斗的步伐;危险与枯燥,消磨不了与毒品斗争到底的意志。
出生于警察家庭的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队长李冬(化名)是在禁毒一线战斗了十几年的老侦查员,他不怕与毒贩生死搏斗,也不怕毒贩的恐吓威胁,但他怕出任务回来时少一个人,“那怎么跟他们的家人交代”;
身患癌症、走出病房继续与毒贩斗智斗勇的女子侦查组队员任莎莎是化装侦查的高手,面对狡黠的毒贩她临危不乱,一次次于险境中给犯罪嫌疑人以痛击;
驻守在木康边境检查站的年轻民警钟履鹏在日复一日看似枯燥的查缉中,始终保持着一股韧劲,曾在大年三十晚上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生生在28吨木炭中查获93公斤毒品;
……
无声的较量,在一幕幕上演;奋斗的接力棒,在一代代传递。
在瑞丽的姐勒新警培训基地,我们见到了刚刚加入这支队伍的年轻面孔。
2000年出生的藏族姑娘尼玛·群卓来自西藏的日喀则。“认识毒品,还是通过之前看过的《中华之剑》的纪录片。”尼玛·群卓说。
从警后,她第一次真正见到吸毒人员,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身上散发着臭味,皮肤上很多伤。“心理上,多少还是有些不适感。”经过6个多月的新警培训,她现在已经可以很从容地应对。
相比于尼玛·群卓,从小在瑞丽长大的王晴则司空见惯。她回忆,小时候周围就有吸毒人员。

从大学校园来到边境一线,年轻的他们踏上了新的赛道。
来到尼玛·群卓和王晴的宿舍,整齐的床铺上被子叠成“豆腐块”,衣柜里整齐地挂着警服,没有多余的装饰,甚至看不出女生宿舍的痕迹。
是想象中的警营吗?会觉得单调乏味吗?她们摇摇头,开玩笑说:“很多时候忙到没时间想这些。”
走出宿舍,前面有一片园子,名为“励警园”,奖杯形状的雕塑上展示着一等功臣、二等功臣事迹,“英雄树”上挂着优秀民警的事迹和座右铭。
王晴指着其中的一棵树说:“上面挂的就是我的榜样。我希望有一天树上也有我的名字,我也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行走在云南德宏边境禁毒一线,我们被流血牺牲的悲壮冲击着,也被与毒品斗争到底的信念感染着,这一切汇聚成一曲前赴后继的战歌,澎湃激昂,生生不息。